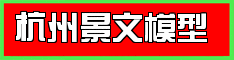一個抽象的超結構橫空出世,以一股勢不可擋的生長力量,不斷地吞噬并占據紐約繁華的城市圖景,僅留下一批建造于建城初期尚未有單一計劃時代的舊式摩天大樓。當我們從海灣俯視這座被連續的尖角紀念碑重新規劃的紐約,會發現這個被視為現代化代表的都市變成了平淡無奇的冰、云與天空……
這個夢魘般的畫面是意大利建筑小組“超級工作室”在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《連續的紀念碑(紐約新象)》里所描繪的未來景象。“超級工作室”的紀念碑與我們熟知的那些擁有紀念性、禮儀功能以及永生意味的紀念碑截然不同,這些網格(Grid)或鏡面的單一建筑結構將侵占我們的城市。借這系列作品,“超級工作室”邀請我們設想一種未來的可能性,在消費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巨浪裹挾之后,我們或許將生活一個在均質、單一、冷漠的網格世界之中。
“超級工作室”所處的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,建筑界熱衷于探討紀念性(Monumentality)與巨構建筑(Megastructure)。與他們的時代同行者尤納·弗萊德曼(Yona Friedman)以及日本新陳代謝派(Metabolism)不同,“超級工作室”當時嘗試以一種反諷、批判的態度抨擊現代主義以及國際風格建筑,并讓自己從消費主義與全球化的禁錮中逃逸而出。
1969年,“超級工作室”發表了一篇類似于行動宣言的文章,他們袒露:“我們深信建筑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工具,可以使宇宙秩序顯現于地球,可以讓萬物以律而行,可以確保人類言行順應理性。在“溫和的烏托邦”中,未來所有建筑皆出自單一行為、單一設計,能夠一勞永逸地厘清人類架起石墓、石碑、金字塔,規劃方形、環形、星形城市以及在沙漠中(最后奮力一搏)劃出白線的種種動機。”所以,他們開始通過“單一設計”,豎立起一座座全新“連續的紀念碑”,并依此創造萬物。“超級工作室”堅信這種僅為自身或理性所用的“理性建筑”(Architecture of Reason),是技術性、神圣性與功能性三者的結合,也是人類、理性結構與歷史的結合。
“超級工作室”提到的“唯一設計”(Single Design),是將具象的世間事物消退成為一種抽象的概念物,它不具有任何特定語境與意義,是一個純粹理性物。早于他們的《建筑直方圖》(Histogram of Architecture )作品中,他們便將方格通過3×3厘米、30×30厘米或是3米×3米的尺寸進行延展,設計《測量》(Misura)系列家具與實體建筑《超級工作室景觀辦公室》(Landscape Office)。網格元素也出現在“超級工作室”的《連續的紀念碑》系列作品中。他們讓網格的巨構紀念碑穿越山巒、海洋與土地,橫跨城市與歷史遺跡,最終覆蓋了整個地球。
《連續的紀念碑》是“超級工作室”為了1969年格拉茨雙年展構想的作品,那屆主題名為“建筑與自由”。“超級工作室”在展覽上首次對公眾呈現了《連續的紀念碑》的彩色插圖,他們對這系列作品懷有一個遠大的愿景,希望能夠將其拍攝成為一部影片。雖然最后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這個想法,但是他們將拍攝準備時創作的逾90個分鏡腳本整合成了一個故事。在PSA“超級工作室50年”展覽中,向觀眾們呈現了盧斯奧·拉佩特拉(Lucio Lapietra)工作室在2016年為了致敬“超級工作室”創作的影片《連續的紀念碑1996-2016》。這部影片主要源自于那時的分鏡腳本,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實現了“超級工作室”當時的理想。
“超級工作室”在《連續的紀念碑》的故事腳本中首先回顧了開普勒的行星軌道、達·芬奇的人體解剖圖、以及曼荼羅的宇宙觀之中蘊含的基礎理性元素。隨后,他們追尋了多種文化之中的紀念碑,表達了解紀念碑其實是為了填補理性與無意識之間的空隙的概念。通過這兩重鋪墊,他們引入了用一種完美的理性元素“立方體”(Cube)構建全新紀念碑的設想。
在被科技、文化與各種帝國主義同質化的地球,建筑將從單一永續的環境中浮現。 “連續的紀念碑”是一種全面城市化的建筑模型,它們賦予個體擁有現實并實現內心的平靜,守衛古老的紀念碑與歷史遺跡,重新規劃城市的發展,甚至還與自然達成了和解。最終,人們卻將生活在無窮無盡的網格之中。
“超級工作室”以連續的紀念碑規劃的理性世界,傳達了他們反烏托邦的思想,這也是他們給后世的警示。我們是否曾設想過,在未來的某一天,是否會生活在一個均質、單一、冷漠的網格世界之內?